打造百年武术名站,
武风网做有态度的武术网站!

1
我像贼一样,蛰伏在暗室,等待一场经典拳击。
这种心理多少有点怪异,阴暗。就好象小时候闲观别人打架,偷看人家闹房。别人打架你乐呵,他人吃打你喝彩;人家受难你偷笑,人家遭殃你叫好,人家歇菜你激动,人家丧命你祈祷。这不是拳击的本意。果真如此,我倒真有点潸然泪下了。拳击,生龙活虎的美好拳击,竟成了野蛮人的祭祀法宝;人类的强劲冲动,一夜之间,成了野蛮族类的嗜血赌注。
说透彻了,也便感受到了。我倒想说,拳击是人性的生动写真,却何尝不是蛮族的残留冲动。人类和人类相见,非礼一番,你打不斗,青面獠牙,狰狞可怖,两个武装到牙齿的蛮野之人,就像两头发情的野猪,眼瞅苍天,口翻白沫,心里直鼓捣,如何才能打得对手俯首称臣……
夜色苍茫,风华尽失,人类疲惫,生灵顿悟,拳击家门忽然想起了握手致意,礼貌寒暄,骑士风度,绅士风采,夸夸其谈,沾沾自喜,谈话投机,味道上选。
拳击到了这儿,未免沾染了几许蛮野的成色。或许,拳击本身并不蛮野,倒是我等观看拳击大赛的无聊看客,多多少少,有点无端的蛮野。
我于是说,看拳的人,竟比打拳的人还要莫名其妙的蛮野千倍,百倍,万倍,亿倍。于是,我真的是越来越看不懂拳击了。每当我看完了拳击,我必呻吟。"忏悔吧!你这个十足的恶人,只有拳击,才能净化人类污浊的灵魂!"
野语有言之,俗话说得好,善人有善报,恶人有恶报,不是不报应,时辰还不到,时辰一来到,马上就有报。我不看拳击,并不等于拳击的消失。我不看拳击,并不能终止世界的轮回。我忽然想到,拳击的消失,是否预示着一个不再杀生世界的诞生。索性,所有的钢铁战士,放下屠刀,脱离拳击,另立门户,做一个清寒隐士。
想过么?拳击和隐士有何关系?我却认为两者有至深至大之干系。我一直揣摩,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两种人,拳手家式的斗士,和尚一般的隐士。凶猛的拳手,卷起了一阵斗士的风流;飘逸的隐者,引发了忍者好一阵悲歌。甭管你是天王老子,龟孙儿子,谁都逃不掉这两种命运的拷问。
真理,永远是不折不扣的。你想征杀在前,冲锋陷阵,你便是大英雄的候选人。你如若金盆洗手,坐拥世界,展示人生大境界,你便是绝顶大隐士。
说起来,这都是些很不值钱的废话。言谈家的言论只能影响极少数的人,却不可以影响庸庸众生。闲话少说,谈话之间,我听见了锣声,拳击开赛了。时间是2004年的7月4号,倒像是某个国家的国庆节。对了,正是美国的国庆日。同样是美国,太平洋的城市,洛杉矶,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拳击赛,如期开场了。
世界依然是不声不响的。世界的坐标依然闪耀着夺人的光焰。很多人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拳击的要义。美国的这场拳击和欧洲的那场拳击,竟也看不出本质的区别。世界的盲流还在扩军,观看拳击的人,肯定比理解拳击的人,多出几百万倍。
拳击场依然暗淡无光,即使在大白天,也是暗无天日。出场的都是些拳击场上的边角料,十足的无名鼠辈,大煞了很多风景。几个中量级的选手悉数登场。那真是,老瓜伴茄子,秧苗伴韭菜,弄得人没了一丁点儿的脾性。中量级的拳击,即便全都是世界上顶级的拳手,顶门上杠,搬砖上窑,也是鸡肋。那叫做,弃之可惜,食之无味。
我似乎仍然钟情于重量级的拳赛。比如前几天的泰森出场,38岁的年纪了,终于懂得了人生的真谛。泰森第一次没有剑拔弩张,竟和他的对手握手拥抱。那副憨厚的表情,叫人动情。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拳击的温情。猛兽的泰森,变成了隐士的泰森,竟也是一分钟内的事儿。十年前,谁敢相信泰森的温柔!
电视机还在喧闹,我看清了,亮相的都是美洲人,泰勒对阵马奎斯。那叫做,近水楼台先得月,好汉落难鬼推磨。十人九痔有来历,马达声叫人头落。
近些年来,好多拳击家都云集美国混日子。就好象19世纪的画家,云集巴黎闯天下。30年代的作家,麇集上海打世界。当今的京华大地,10万北漂闹革命。一切的一切,全都为的叮叮当当的俩字儿……机会!出头的机会,做人的机会,称王称霸的机会,杀生成仁的机会,肝脑涂地的机会,血流成河的机会。成全的机会,跟进了毁灭的机会。美妙的机会,追杀住丑陋的机会。一切的机会,都是为了决出一张生死薄,阎王小鬼闹汹汹。
2
泰勒太狠了,出手就是霸王鞭。出鞭,击鞭,收鞭,格鞭,灵敏得好似一只美洲山猫,凶狠得仿佛一只战地螳螂。有人说,以他的实力,打败金童霍亚,没问题。果然,刚打到9回合,马奎斯吃了几记重拳,犹如一只触电的蜘蛛,歪扭歪扭地倒下了。裁判一声断喝,终止了喧哗的比赛。一切的一都宛如当年的猛张飞,喝断了当阳桥。
我依旧不忍心观看这场悲壮的拳赛。太血腥的场面尚未出现,我竟将拳击场看成了屠宰场。野兔野羊,一律割杀。剥皮抽筋,剔骨洗肠。自古牛羊一棵菜,天然食物人人爱。一天不吃不要紧,十天不吃想不开。拳击,总是那么惆怅,叫人寝食难安。
也恰好,昨天晚上,央视一套的《人与自然》刚刚播完《螳螂》。电视片把螳螂看成了昆虫里的豪杰。传说李小龙就是凭借几招仙鹤拳、螳螂拳打进美国电影界的。
螳螂,十足的昆虫大侠。17世纪,中国的王郎观察螳螂打败麻雀,发明螳螂拳。从此以后,中国武术出现了惊天大蜕变,螳螂拳成了中国武术的一大流派。
我早就说过,拳击的发力方法最像螳螂拳。五分之一秒,搞定了所有的猎物。难怪美国人把螳螂拳看成中国拳术的极品,将其列入与太极拳、形意拳、少林拳、八卦掌对等的拳种。
侠客出手,看的是无刀胜有刀。拳手出拳,图的个来去无踪影。战无不胜,固然神气飞扬,不战而屈人之兵,乃是神奇大境界。谁想来个肝脑大涂地,谁便做不了天地大隐士。泰勒出手,要的就是个身正影不歪。马奎斯倒地,图的个全身而退,隐忍终身。
拳赛结束了,世界并未结束。电视里旋即转播起了萨达姆受审的镜头。萨达姆说:“这是一场戏,受审判的应当是布什,不是我!”审判的人马并未歇手。坐在审判椅子里的仍旧是萨达姆,还不可能是布什。当年,萨达姆也说过:“我情愿和布什决斗。他拿他的汤姆冲锋枪,我拿我的阿卡冲锋枪,咱们靶场见面,一死方休!”萨达姆是条汉子,至少很像条汉子。可惜了,布什没有迎战。一场最经典的决斗,还没来得及开打,便匆匆画上了句号。
谁来为萨达姆平反?没有人会为他昭雪。强权只讲强权,从来蔑视公平竞争。只有拳击讲究公平。职业拳击玩的就是赤裸裸的光板脊梁,煽动起人类的好斗天性。
霸业是永恒的,称霸的过程却极其漫长。得意的人是嚣张的,受审判的人却愁云满面。人,所有的人,生来就具有贪欲的人,只有为了自由才走向冒险,又为了冒险才失去了自由。这便是萨达姆之路,也是马奎斯之路,它何尝不是所有热爱讴歌生命的热血斗士之路。
爱,自由,美感,强烈的感官释放,那才叫超级的江湖风韵。拳击,是江湖的边缘。只有失去爱与美的人才会变成侠客。李白,中国的大唐诗仙李太白,大笔一挥,挥洒成一首《侠客行》
赵客缦胡缨,吴钩霜雪明。银鞍照白马,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,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袖去,深藏身与名。闲过信陵饮,脱剑膝前横。将炙啖朱亥,持觞劝侯嬴。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。眼花耳热后,意气素霓生。救赵挥金槌,邯郸先震惊。千秋二壮士,煊赫大梁城。纵死侠骨香,不惭世上英。谁能书阁下,白首太玄经。
听说李太白是擅长格斗的,还亲手杀死几名亡命的歹徒。那真是绝顶的豪情。一介文人,竟然斩金如土,削铁如泥,快哉快哉!我早就说过,拳击是青春的象征,李太白也是青春的象征。只有侠客才会怜惜人间众生,惟独隐士才会想起林莽的雄奇。一位中国的拳手,只要背负一把宝剑,便可行走天下。大江南北,山水河湖。逢山开路,遇水搭桥。果敢的心,包藏住醉汉一样的热情。我们一同醉倒在江天一色的秋天。
云,我最爱之云,只是拳击的一枚扣子。拳击还要打下去的。拳击的要义就在于人类暂时忘却了世界的存在。人类行同陌路,彼此全不相识。拳击夸张了人间的敌意,强弓拉硬马,楞是将一大堆的莫名其妙的财富,化做了晚天的云霓。
可惜,拳手只是一种工作,甚至是极度卑微的工作。泰森的文化并不高,泰勒也绝对不会获得诺贝尔奖金。拳手的生存空间狭小得可怜,容不得半点的喘气机会。拳击,即是死亡之后的丛林。高卧云林的江湖隐士,已经不再追寻拳击的真谛了。
听说,男人过了四十岁就不再看拳击了。大约因为社会人生的超天大决斗,大多淤积在人类男儿的四十岁左右。四十岁的男人本身就是决斗的参与者。只要你活着,你必然决斗。这是科学中的科学,真理之上的真理。四十岁的男儿,本身就置身于蛮野的江天,缘何还要观看更加蛮野的拳击。
徜徉于蛮野的人,绝对不会讴歌蛮野。观赏拳击的人,渐渐地不在依恋拳击。拳击的销魂一刻,正在变得模糊不清,混沌未明。我终于看出了拳击的野蛮,拳击也还原了蛮野的天性。
春晓一刻值千金,拳击的原型,并不仅仅属于精神的独享。自由的极限,一直没有遗忘演绎江河一统的快感。这都是些常识,都是不争的事实,也是比天理还像天理的天理。
到底谁是强者,答案必然出笼。拳击的看客,拳击的缔造者,谁都不愿无限期失语。
3
隐士是不看拳击的,真隐士更是不屑于拳击。世界的核心的江天,还是拳场,都还是天然的谜语。即便是强者,也必有更强的强者,用于征服眼前的强者。这便是拳击的悲剧,也是隐士的萌芽。这便是拳击的终点,也便是隐士的起点。
泰森并不懂得隐士,所以他才是拳击家。泰森也即将迈进四十岁的男人了。那真是个极佳的年纪,男人四十一朵花,女人四十豆腐渣。我始终认为,男人四十,才是他的如花岁月。
如花,应该是个很美的名字。李碧华的《胭脂扣》,应是拳击的一面镜子。那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。拳击能如花么,显然能,也显然不能。
记得我曾经像野狼一样憧憬过拳击的全盘景致。野狼,一群坦克一般的野战狼群,奔波在雪域,那是我最向往的野蛮生活。多少年了,我一直怀念的就是野狼。记得一位作家写过一部《怀念狼》,多温情的名字。我们多少年都没见过这样好的记忆方式了。纪念狼,仍旧是对人类最好的纪念。正如纪念拳击,仍旧是对人类的祭奠议程。
我不是唯一的拳击动物,拳击也绝非人类的特殊专利。听说,袋鼠的拳击技术就很过硬,大猩猩的拳击姿态就很优雅,螳螂的拳击速度是拳击的极品,即便狗熊的拳击水准也高出人类的惯常的想象力许多倍。
我热爱动物,伊始热爱拳击。我们鼓吹进取,伊始依恋拳击。拳击是人类外向性情的衍生物,拳击是人类超越平凡生涯的助推器;拳击是人类施展心灵自由的非凡大羽翼,拳击是人类关爱世界的独门大法器。
套用一位诗人的语言,我必说,拳击,我想起了你,就饶恕了自己。饶恕了自己,也便饶恕了这个世界。诗人们一贯爱好古怪的想象。写诗的李太白一直怀念拳击遗留的所有的证据。王者归来,归兮来兮!天色将晚,胡不归!拳击的声音始终难以穿透时空的疆域。
飞墙,踢腿;月落,捉贼。天生我才必有用,我辈岂是蓬蒿人。王者的意志,贯穿于宇宙的疆野。隐士们长久的风花雪月,挑起了大红灯笼下唯一的光明。拳击,惟独拳击,成了崭新空间的死亡预设。投降吧,拳击,面对霜天万木。谁取得了天下,谁便是王者。王权理论从来就会眷顾幸运的拳手。
我歌,我悲,我喜,我泣,都为了王权下非常的阴影。解脱过后,冲杀的盲区。惟余晴天一日,映照万类霜天。还有什么理由不愿意放弃。做一个超级的大隐士,绝对胜过真正的拳击家。或者,最伟大的拳击家都是最伟大的隐士。隐士是对人类意志的解脱。拳击是对人类肉体的解脱。隐士是放弃了人生的规范,拳击是捍卫了人民的尊严。隐士是长者的长歌,拳击是少年的吟唱。隐士是智者的雅趣,拳击是精神的皈依。拳击是闹市的驼铃,隐士是深山的鸟鸣。拳击是火海的沥炼,隐士是常规的超人。
拳击的风流,也正是隐士的风流。面对霜天,我们已经穷尽了思维的张力。拳击家们的铿锵声正在消逝,隐士们的柴门也刚刚关闭,等待秋天里的第一场雪,竟也是剑阁峥嵘,鬼门无依。
泰森的肌肉已经算不得最美好的肌肉了。刚才还见到了世界大力士比赛,壮硕如牛的男人,谁都比泰森强健。所有的极品都在等待更大的极品去淹没,吞噬,消解,毁灭。何况拳击之外的边缘,还有更大的边缘。
隐士,就是拳击的边缘。隐士的理想,就是拳击的理想。隐士的终极法则,就是拳击的终极法则。我们几乎淡忘了所有的拳击过程。我只想说,大侠客们背负起青龙宝剑,大隐士啜吸起一杯清茶,山大王背负起新拐的压寨夫人,拳击家只需一只厚厚的拳囊,便可踏浪无迹,纵横天下。我们都是经典的隐士,为了精神的沦落,走到了高峰低潮,峡谷险滩。他们都是人类的弃儿,为了爱的追寻,行走在刀山火海。
梦归故里,就像一枚点亮的灯塔。隐士们的家乡,同样的鲜花遍野。还有那几位热爱过拳击的人,梦里依稀,聆听拳击的节奏。拳击是个很叫人痴迷的游戏。呆头呆脑的拳击迷们,就好象折断了翅膀的鸟,掉进了孤寂的洞穴。拳击家和隐士都很孤独,他们是真正的孤儿,或许因了同样的孤独,伊始走到了同一条黑暗的地洞。孤灯,霜天,万籁俱寂。李太白的《侠客行》终有它过时的时节。我更爱隐士的哲学。还是说说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为好。
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那是真正的隐者之声。泰森是听不懂这首歌的,我深深地为泰森遗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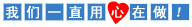
资助鼓励
如果您认为我们做的对您是有价值的,并鼓励我们做的更好,请给我们关注和支持!